生活菜园
英国18岁议员因政务繁忙频繁逃课 被学校开除
英国18岁议员因政务繁忙频繁逃课 被学校开除
据英国媒体24日报道,18岁的英国纽卡斯尔区议员凯尔·泰勒(如图)由于“公务”繁忙,频频“逃课”出席各种政府会议而被所在的学校开除,成为该国为数不多在校期间被开除的政府高官。
身为工党人士的泰勒于今年5月被选为议员,政务繁忙的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出席各种会议。不过他所在的玛丽希尔高等媒体艺术学院并没有因为泰勒的特殊身份而对他网开一面。
该校校长艾伦·琼斯接受采访时气愤地表示,从两年前开始,泰勒议员就一直以各种理由缺席课程,今年3月以来,其出勤率甚至不足50%。
琼斯透露,校方在3月份就给予泰勒一份书面警告,但他一直置之不理,学校忍无可忍之下,在日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通知泰勒议员,上完这一学期后他就不用再来了。
对于校方的举动,这位年轻的议员表示难以接受,他辩称自己自当选议员后只缺席过总共6小时的课程,没有校方说得那么夸张。
据悉,泰勒本来计划在完成这一学年的学业后即申请参加英国高等教育考试。不过现在他已被开除,只能再寻觅一所学校,重新开始备考。目前尚不知此事对泰勒的仕途有何影响
国企工人在车间挥刀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
国企工人在车间挥刀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四角
核心提示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随即发生。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更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地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还过得去。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的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同是车间工人的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为了生活,耿田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渐渐有了起 色。如今,他们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和工厂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所有工资加起来,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元。作为朋友,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可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贷,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潘鸿强也想过改变,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门。”耿田刚说。
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终日子越过越拮据。“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荡荡地,啥都没有。”耿田刚说。
而他又好面子。红白喜事,别人要掏二百,他咬咬牙,也要掏。“他爱充大头”,工友的妻子这样说。
而在朋友眼中,潘鸿强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心性强,在人跟前从不示弱。谁想在他跟前说风凉话,没门!”耿田刚说,虽然潘鸿强对人都很和气,脾气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这个在朋友眼中“很硬气”的男人,平时的爱好是喝点酒。
今年春节,他们两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鸭。那次他看起来还算高兴。“多年没见他开心了!其实有啥开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车。去年,要分房了,本来是高兴的事,对他,倒成了灾难。买了一屁股债。”耿田刚叹息着。
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不习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夫妇俩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1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 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 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 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翻不过身来”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孤独者”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都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这个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 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 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
富裕阶层纷纷赴美产子 孩子落地即美国公民
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只要在美国领土出生都算美国人,这催生越来越多外国人选在美国生产,以让孩子获得美国籍。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频繁,许多“台湾 经验”都在大陆复制,其中用观光名义到美国生个美国籍小孩就是其中之一。把生“美国人”当投资,促使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准妈妈也投身于“生子游客”大军 中。对于赴美产子之风盛行,美使馆发言人形容,这并不犯法——富裕阶层掀赴美产子热
中国的富裕阶层中近年掀起赴美产子热,协助办理此类事宜的顾问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越开越多。行内人形容,中国人希望子女生而之成为美国公民,是希望孩子能享受到美国的教育制度以及社会环境。
美国《星岛日报》援引《华盛顿邮报》消息指出,在众多产子旅游顾问公司中,创办时间最长的,是由一对侨居上海的台湾夫妇所开设。公司会安排即将临盆的母 亲,以“产前两个月产后一个月”的形式,在加州的育儿中心住3个月,中心内所有医生护士都说中文,房间设有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每天收费35美元,此外还包 括观光和购物行程。公司标榜,整套服务基本收费只是1475美元,这个价钱连汽车、钻戒都买不到,却可以为顾客的子女以至全家换来美国公民身份。公司同时 表明,服务并不包括赴美机票和申办旅游签证,他们充其量只会协助填写表格。
公司的创办人周氏夫妇坚称,他们绝非“蛇头”,只是利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赋予的出生公民权,协助中国大陆和台湾客户令其子女成为美国公民而已,客户的家境都相当殷实,无意在美定居。
今年1月经这对夫妇安排到美国产子的王女士形容,自己的哥哥和姐姐都曾留学美国,当时家中付了极昂贵的学费,如果孩子有公民权,升学时无疑多一项选 择,孩子升学的费用就便宜多了,与丈夫都是来自台湾的她说,美国地广人稀,而且没有污染,居住环境也理想,至于他们自己,除非晚年,否则也不会迁居美国。
对于赴美产子之风盛行,美使馆发言人形容,协办产子旅游的顾问公司,性质其实与协助办学生签证的机构差不多,最多只能说他们是在利用法律漏洞,而美国政府方面,国会既没有为此立法,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也没有针对怀孕的外国访客定下特别的政策。
生“美国人”当投资
美国是为数不多给予在本土出生人士公民权的国家,拥有美国籍后可享受的种种“特权”,是“生育之旅”(Birth Tourism)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美国《侨报》此前报道称,近年来,各国到美国待产生小孩的准妈妈趋增。这其中也不乏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准妈 妈。三四个月之后就能把最有价值的纪念品“美国孩子”带回家,几乎赴美生育的中国父母们都认为花2万多美元,对子女来说是人生最值得的投资。
根据美国的福利制度,一个孩子如果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就等于拿到了进入社会安全系统的钥匙,尤其是教育。这个孩子长大后能自动报考美国大学,而且更容易申 请只面向美国本土学生发放的助学金;此外,孩子的父母多年后可依照宪法获得美国社安待遇。美国移民政策允许本国公民申请外国籍父母、配偶、未成年和成年子 女来美定居。这个孩子一旦年满21岁,上述亲友即有资格获发签证,因此即便是如此漫长的等待期,也不会令他们却步。
来自上海的谢太太,5月曾在包下豪华单人房月子中心待产,预计将花4个月在美国生孩子兼坐月子,包括医院自费生产和机票等花销预计将支付3万美元。 《星岛日报》指出,已在圣盖博市(San Gabriel)住了两个月的谢太太对月子中心非常满意,在中国做生意的谢先生也将赴美陪太太迎接他们第一个孩子,谢太太认为,这是为了孩子一生发展的必 要投资。
大陆复制“台湾经验”
近年来,中国两岸交流频繁,许多“台湾经验”在大陆复制,用观光名义到美国生个美国籍小孩就是其中之一。美国《世界日报》援引《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来自 中国台湾的赵玲伶跟老公周先生5年前在上海创业,专办“生产之旅”,是大陆最早经营这种生意的业者。他们安排大陆有钱的准妈妈前往美国待产,已成功让五六 百人顺利成为美国人的妈妈。
依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及相关法规,在美国领土出生自然拥有美国国籍,年满21岁后,就可申请其外国籍父母赴美定居。赵玲伶自己就是专程到美国生产,因 此察觉“生产之旅”在大陆的商机。过去入住该公司坐月子的孕妇八成来自台湾,现在光是北京及上海的客户就占了七成。赵玲伶的老公周先生称,大陆客户都是经 济富裕的医生、律师、企业领袖、知名媒体人等,“他们搭头等舱赴美”。
委托赵玲伶代办赴美生产的朱女士说,教育及生活环境是主要原因,要提供小孩另一个选择机会,有了美国籍在美国念书比较便宜。她说,她们夫妇目前没有想要移民美国,“也许等退休以后吧。”
老照片:毛主席的芒果到沈阳 68年文革狂热记录(组图)
老照片:毛主席的芒果到沈阳 68年文革狂热记录(组图)
 |
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又被传给了沈阳的工人阶级——“送芒果”事件轰动一时,芒果被群众当作圣物供奉。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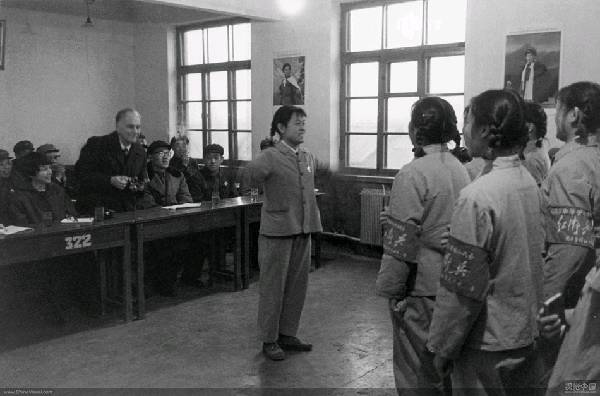 |
| 埃德加·斯诺访问沈阳,观看群众表演。 |
 |
| 车厢里的“三忠于”右一为当时全国家喻户晓的学毛选女积极分子张XX. 1967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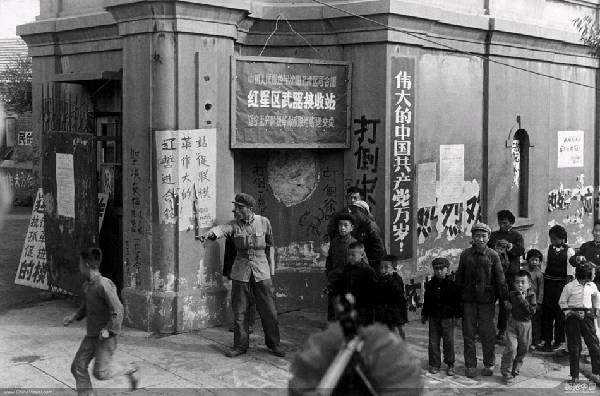 |
| 革命群众庆祝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 |
 |
| 革命群众在批斗现场学习毛泽东语录时让走资派面壁. 1967年。 |
 |
| 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盲人积极分子在发言. 1967年。 |
 |
| 举着漫画的游行队伍. 1966年。 |
 |
|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和陈锡联在一起。 |
 |
| “革命群众”在斗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 1967年。 |
 |
| 在营口市的“万人坑”召开批判大会(1967)。 |
前东德摄影师遭禁照片公布 真实东德百姓生活(组图)
前东德摄影师遭禁照片公布 真实东德百姓生活(组图) 
照片中这些位于罗斯托克的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其样式是当时东德比较典型的。这种建筑的发展只体现在住房的数量上。弗里德·威腾博格在1981年拍下这张照片。
国际在线专稿:据《明镜》周刊网站7月20日报道,东德摄影师西格弗里德·威腾博格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一组照片被认为反映了“东德单调乏味的生活”。因此原东德政府曾禁止他展出这些摄影作品,实际上这些照片只是反映了当时东德老百姓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片段。
1990年的罗斯托克,生活在这些建筑中的民众抱怨称,自己好像住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只要一下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便会变得泥泞不堪。
罗斯托克市民蹒跚着走过铺设的木板,返回他们的新家,远处的居民楼是刚刚建好的。
居民区里用于晾衣服的公共区域
威腾博格于1987年拍摄的一张照片,这是一个旅馆外的牌子,上面写着“我们期待您的惠顾”。
罗斯托克一座典型居民楼的单元门口。
这是罗斯托克的一家理发店,照片拍摄于1988年。
在东德的饭店里,顾客显然不是上帝。每家饭店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如果顾客不遵守就得不到服务。前面的牌子上写着:不要改变桌椅的顺序。
在一家商店的门口,顾客正在排队。人们总是急切地问着商店里有什么东西;或者压根就不问直接排队,因为提供的货物量都很短缺。这张照片拍摄于1987年的耶拿市。
悉尼地产商谋杀案有进展
曾震惊一时的悉尼百万地产商Michael McGurk当街被爆头命案的调查取得进账,警方相信他们已经知道杀手身份。
据警方消息人士透露,Narrunga行动组要找的疑犯是南美洲人。他受雇谋杀McGurk,在案发后24小时内已经逃离澳洲。
去年,45岁的McGurk于其Cremorne的Cranbrook大街住宅外停车时,被人一枪打中后脑勺身亡,他10岁大的儿子目睹整个过程。
凶器怀疑是一支小口径手枪。
案发数天后,死者被爆与多起房地产交易法律纠纷及恐吓殴打事件有关。这些事件都是调查的重点。
还有报道指,死者拥有涉及政府及政客在悉尼西南区土地交易受贿的秘密录音带。但廉政公署(ICAC)的调查没有找到相关证据。
堪培拉一民居惊现自制炸弹
一名堪培拉男子周二在法庭上被指控拥有危险武器和制造炸弹等罪名。
据悉,周一接到举报后,警方赶至位于堪培拉城市中心Ainslie Village的一处民居,发现大量危险品。其中包括化学药剂、炸弹、导火索等制造炸弹用材。
警方随即决定现场进行封锁,并疏散附近居民。紧急应对专家小组和炸弹拆卸队迅速来到现场,处理炸弹、炸药等危险品。拆卸队前后一共发现并成功拆除三个爆炸装置。
随后,警方宣布该民居及其附近区域恢复安全状态。
这名31岁的男子周二在首都领地地方法院出庭,被控拥有和使用违禁武器以及使用爆炸装置威胁生命等罪名。
该男子被命令进行精神病检查。
工党承诺拨2.77亿元防自杀
吉拉德总理(Julia Gillard)今日承诺,如果工党赢得联邦大选的话,将拨款2.77亿元用于防止自杀。
吉拉德今日在布里斯班“社区经济发展协会”(CEDA)发表讲话时表示,这笔拨款将用于支持社区、学校、医疗中心及护理人员更好地防止发生自杀这样的悲剧。而这2.77亿元将主要用在四个重要领域:前线服务、预防执导、危机干预以及针对男性及儿童的精神健康服务。
吉拉德强调,在工党的第二个任期中,精神健康将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工党每年将为约1.25万名意图自杀或有自杀倾向的民众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每年在社区内还将举办多达2万场心理讲座。
此外,政府还将大力扶持严重精神疾病的治疗护理,例如为日常护理服务提供协助,以令那些照顾严重精神病患的人士能有休息的机会。工党还会特别专注预 防自杀指导以及危机干预。预防自杀热线Lifeline将升级以便能接听更多的话,民众今后还能通过手机直接免费拨打该热线。在自杀多发地区,当局除了将 设立专门的热线外,还会在悉尼的The Gap等地区进行安全升级工作。
吉拉德表示,当局还将向受到自杀事件影响的学校派遣心理服务小组。以便减少发生有样学样的连环自杀事件。
工党的预防自杀计划的重点还将放在男士身上,因为吉拉德认为男性虽然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更大,但是寻求帮助的几率反而更小。
改善儿童精神状况的服务也将有所拓展。吉拉德称,培训教师、家长、前线护理人员以及社工以帮助精神健康问题、发育问题以及行为问题严重的儿童,也将是工党的重点。根据工党的计划,不愿或无法进行面对面心理咨询服务的年轻人,还将能够在网上接受心理辅导。
被指反对带薪产假 吉拉德疑遭背后一刀
根据9频道电视台记者Laurie Oakes得到的政府内部机密,当陆克文还担任总理时,吉拉德曾经对带薪产假计划和养老金增加表示质疑。
据称,吉拉德曾在内阁中反对18周的最低工资带薪产假计划。这项计划将在明年1月份开始实施。
Laurie Oakes表示,吉拉德当时向内阁指出,将带薪产假计划作为一项政治砝码是错误的。她说:“那些过了生小孩年龄的母亲会非常气愤的并讨厌这样的政策,特别是一直呆在家中的主妇们。”
吉拉德还被爆曾质疑每周30元的单人养老金增加计划。这一养老金调整草案,是自养老金制度确立以来最大幅度的增加。
Oakes称,根据政府的这份秘密报告,吉拉德当时质疑的不是养老金增加,而是这140亿元的成本,她说那些老年选民并不支持工党。Oakes还暗示,这些资料不是从反对党手中拿到的,而是来自工党内部。
前总理陆克文表示,这份Lauries Oakes得到的政府机密并不是自己透露的。陆克文发言人称,他没有也不会透露内阁会议的机密内容。但根据《悉尼晨锋报》报道,机密泄露的来源是政界人士。
对此,工党大选委员会代表吉拉德发布了声明:“内阁会议内容是机密的,我(吉拉德)也总是保守这些秘密,并且将继续保守下去。任何匿名的指责我都不会回应,如果自由党做出这样的指责,他们至少应该署名。”
反对党领袖艾伯特表示,吉拉德的真诚应该遭到质疑。
澳媒头条:中国国企在澳被控贩运华人奴隶做苦力(图)
澳媒头条:中国国企在澳被控贩运华人奴隶做苦力(图) 澳洲日报
澳媒头条:中国国有公司在澳洲被控贩运华人奴隶做苦力
澳大利亚法定最低工资是15澳元一小时。
中国一国有企业SANAN(中国三安建设工程公司)从中国雇佣了24个人来重体力,每小时1.9澳元,被工人权益委员会给告到法庭了。



阿德雷德《广告人报》18日报道,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中国三安(音译,SANAN)工程建设公司”因违反澳洲劳资关系法2项规定,正受到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的调查。
这家公司引进了24名持临时居留签证的中国籍劳工到阿德雷德拆除并搬运原澳洲三菱汽车公司使用的汽车压床等重型机械。工作非常繁重,但工人们的时薪 却只有1.9澳元。这些华工从去年10月29日起到今年6月底,在位于阿德雷德Tonsley公园的工厂工作了8个月,期间他们一直居住在阿德雷德的一间 集体宿舍中。该中国公司至少少支付了他们13.1万澳元的薪酬。
目前,公平工作委员会已经把该公司告上法庭,指控其违反了澳洲劳资关系法的2项法规。公平工作委员会执行长坎贝尔(Michael Campbell)表示,该公司在与华工们签订的合同中说明,劳工每月工作21.75天,每天7.6个小时,并有权获得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在本案发 生期间,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是14.31澳元。但中国三安实际支付给工人的时薪介于1.9和6.75澳元之间,折合月薪从2005到6603澳元不 等。
坎贝尔说:“公平工作委员会致力于确保海外劳工享有与澳洲劳工相同的待遇,并会对那些剥削海外劳工的雇主们采取法律行动。这类信息需要被强劲且持续地传达给雇主,以阻止这种行为。带有剥削性的做法是不可容忍的。”
澳洲制造业工人工会(AMWU)早已得知此事,但在对此展开调查时却遭遇重重阻挠。AMWU南澳书记卡米罗(John Camillo)对中国三安支付1.9元的时薪表示愤慨,称这种行为“可耻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说:“该公司很清楚澳洲的劳资关系制度,我不明白他们为什 么要这么做。我们曾在去年12月对工人的待遇展开调查,但却四处碰壁,该公司告诉我们,那些中国人不是劳工,而是工程师。公司还阻止我们接近他们或者与他 们交谈。这是件可耻的事,有很多人明明知晓内情,却坐视不理。该公司对工人比对奴隶还残酷,每小时只付1块多澳元也太过分了!我们将进一步调查此事,并确 保它永远不会再发生。”
公平工作委员会是在接到移民局的知会后介入本案调查的。反舞弊专员于今年年初多次走访了前三菱汽车织造厂,其中1月份去了两次,2月份三次,5月份一次,并采访了华工、中国三安的代理律师和澳洲三菱公司的代表。
据悉,这24名华工最初都是持456类签证来到阿德雷德的,但该类签证只适用于“为期3个月的特殊、非持续性的短期商务考察”,因此移民局后来以违 规为由取消了这些签证。但部分华工随后又持允许在受监督情况下工作的457签证返回了阿德雷德。中国三安以“出国旅行补助”的名义在劳工返回中国后向他们 发放劳动报酬。



